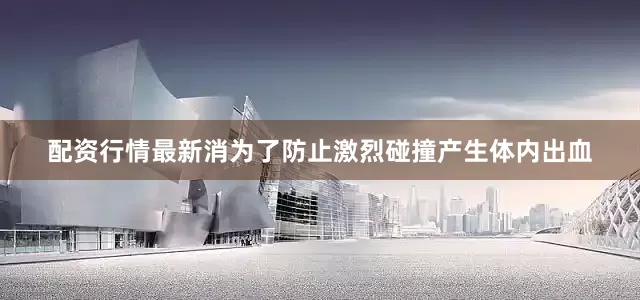自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5月21日,中国人民志愿军接连发起五场规模宏大的战役。尽管我军一度逼近三七线,但最终防线依旧稳固在三八线。鲜为人知的是,志愿军亦曾筹划发起一场气势磅礴的第六次战役。然而,由于诸多因素,尽管我军为此役投入了巨大心力,最终还是未能付诸实施。

在第五次战役的后期阶段,面对“联合国军”的猛烈反扑,我军防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,承受了惨重的损失。在这场战役中,我军伤亡人数高达8.5万,被俘人数亦急剧攀升。第五次战役后期的挫败,逐渐揭示了新中国与美国在国力上的显著鸿沟。原本旨在将“联合国军”驱逐出朝鲜半岛、协助北朝鲜实现全国统一的愿景,已变得遥不可及。
5月30日,彭德怀致信朝鲜人民军总指挥金雄,在信中他特别强调:
“回顾历次战役,美英军依旧展现出强烈的战斗意志。鉴于我们目前的条件,要每次战役中消灭其一个或两个师级部队实属不易,即便消灭一个或两个整团亦非易事。相较之下,伪军的战斗意志较为薄弱,一次战役中将其两三个团击溃则是可行的。要将美英军的战斗意志降至伪军目前的低水平,尚需相当长的时间(约半年至一年)进行充分准备。”
因此,志愿军将战术从运动战调整为阵地战,致力于稳固防线于三八线附近。在此过程中,中朝方面亦与美国展开了接触,并在开城启动了停战谈判的进程。

尽管停战谈判已然启动,然而“联合国军”凭借着强大的战力和猛烈火力,仍旧野心勃勃,意图在志愿军面前彰显武力,力求通过军事上的胜利,迫使我国军队签署屈辱的城下之盟。正因如此,在谈判桌上,美方代表的态度尤为恶劣,动辄因些微小事而中断谈判。
例如,美方坚持要求在谈判现场必须有一位记者在场,而中朝方面则认为,鉴于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,不宜让记者参与其中。未曾想,这一立场差异竟导致了美方代表的拂袖离去。
尤为恶劣的是,美军飞机竟屡次对中朝代表团的驻地进行扫射和轰炸。常言道,“两国交兵,不斩来使”,而美军的这一行径堪称卑劣之至、下作之极。当我国方面提出质疑时,美方联络官肯尼中校竟悠然吹着口哨。
“你们提到飞机即将到来,能否告诉我这架飞机配备了多少台发动机?”
美国在谈判桌上暴露出其倚强凌弱的无赖行径,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在谈判的细节层面,美方进一步要求,中朝双方必须分别从实际控制线后退36公里至68公里,此要求基于美军所具备的强大海空优势,而中朝方则需做出相应的“补偿”。

面对美军的一系列无耻勒索,中朝代表显然不为所动。然而,好战的美国人却因此感到异常兴奋,他们的代表竟失态地拍打着桌面,狂妄地叫嚣着。
“让武器辩论!”
如此,朝鲜战场的战火再次燃起,两百多公里的战线上,双方再次陷入一片混乱。显而易见,美国人的所谓谈判不过是“假谈真打”的伎俩,他们所谓的和平谈判,实则只是侵略的缓兵之计。
“各司其职,谈打分明。”
秉承毛主席的指导思想,彭德怀着手进行军事部署,于1951年6月底着手策划一场规模空前的第六次战役,预定于8月份展开。
即将展开的第六次战役,彭德怀将军深鉴前五役之得失,决意实施诱敌深入、后发制人的战术。他计划让敌军深入我国境内30公里,从而压缩我军的补给线,随后再发起规模宏大的反击。与此同时,针对“联合国军”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,我军也在训练中融入了攻坚作战的元素,以期在第六次战役中能够更大规模地消灭敌人,并夺取更多阵地。

8月8日,彭德怀向毛泽东发去了电报,详细阐述了第六次战役的战略构想。该构想涉及将19兵团与47军、42军联合行动,其中两个军负责牵制英国、加拿大及土耳其的四个旅,另外三个军则配备炮兵和坦克,协同进行全面攻势,目标是驻扎在铁原的美国骑兵第一师。
与此同时,第9兵团的两大军力正牵制着美军第24师、第25师、第3师以及韩国的附庸部队。第20兵团则蓄势待发,准备突破韩军第6师的防线,向山阳里、华川等地实施迂回攻势。在北汉江以东直至海岸线,人民军的两支军团正展开牵制性攻击。在这场战役中,我军将投入九个军的力量。
面对敌军显著的空中优势,彭德怀提议将新近训练完成的空军十个团部署至平壤机场,以此保障我军补给线的安全。
鉴于敌方将领李奇微已洞察我军“礼拜攻势”的后勤软肋,我军提前将大量弹药、粮食和棉服运送至前线,以规避弹药和补给短缺的风险。

我军对第六次战役的备战情况,自然逃不过美军的敏锐察觉。面对即将展开的激烈战役,李奇微深感忧虑。于是,他下令美国空军对我军补给线实施所谓的“绞杀战”,力求破坏我军粮草和弹药的储备。与此同时,朝鲜半岛遭遇了40年来罕见的严重洪水,这为美军的轰炸行动提供了便利。
不仅如此,李奇微更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,对我军阵地发起了两轮规模庞大的攻势。这两次攻势分别被冠以“夏季攻势”与“秋季攻势”的称号。
不同于前五次的冲突,这两场交战对我军而言是较为生疏的阵地战。自成立以来,我军以灵活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术著称,阵地战经验相对匮乏。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期,德国顾问李德曾尝试过“国门之外拒敌”的策略,却导致了红军的重大损失。如今面对火力远超国军的美国军队,志愿军能否抵御住敌人的猛烈进攻?如果此两战失利,不仅第六次战役的发动将成疑,北朝鲜的安全也可能岌岌可危。
然而,志愿军凭借其智慧迅速适应了阵地战的形式,并巧妙地构思出对抗美军强大火力的一种策略——即“坑道战”。

自7月18日起,“联合国军”集结了三个师的兵力,对我军及朝鲜人民军发起了猛烈攻势。然而,我军与朝鲜人民军早已在地下构筑了坚固的坑道工事,静候敌军到来。部分部队更是巧妙地将两个加深后的防空洞连接起来,形成了一个马蹄形的小型坑道,这便是坑道工事的雏形。
在战斗中,我军主力隐蔽于坚固的防御工事之中,仅派出少数战士负责监视敌情。待敌军炮火休止,隐蔽于洞窟中的主力部队便会迅速出击,对敌进行猛攻。此战术之运用,使我军有效削弱了美军的火力优势,并对敌军造成了惨重的损失。
在“夏季攻势”期间,联合国军付出了约7.8万人的伤亡代价(其中美军伤亡2.2万人),然而在东部战线上仅推进了区区2公里。与此同时,志愿军在中线与西线展开了一系列小规模的反攻,成功夺取了多座美国人的阵地。
听闻“夏季防御战”的捷报传来,彭德怀便断定巩固阵地的问题已不再棘手。鉴于朝鲜地区正遭遇严重洪水,彭德怀毅然决定暂缓第六次战役的部署。
尽管我国军队已决定暂缓攻势,然而李奇微、范弗利特等军方强硬派人士却未肯就此罢休。他们认为,夏季攻势的失利源于战术层面上的失误——过分限定攻击正面及兵力部署过于僵化。因此,李奇微决意于10月1日发起所谓的“秋季攻势”,针对中朝阵地发起新一轮的攻势。

然而,在此次战役爆发之前,我军已广泛推广了在“夏季防御战”中由战士们创新的“马蹄形”坑道技术,并构筑了绵延数百公里的坑道网络。面对敌军的炮火,战士们迅速进入坑道隐蔽;在敌军发起进攻时,他们则勇猛出击,与敌人展开激战。借助这种坑道战术,我军的伤亡率显著降低,而美军除了在阵地前沿留下大量尸体,别无他获。
在秋季的防御战中,“联合国军”遭遇了惨重的失败,损失高达8.1万人。若将夏季防御战中的损失一并计算,总数已攀升至令人难以承受的16万人。对此,布莱德雷上将不禁对李奇微上将投以讽刺的笑意。
“若战争持续下去,或许需耗费二十年的时间方才能抵达鸭绿江。”
历经这两场阵地战的胜利,彭德怀深刻认识到,与运动战相较,阵地战更利于成规模地消灭敌人。相较发动第六次战役,坚守三八线并迫使美军和谈的胜算更大。鉴于此,彭德怀毅然决然地作出决策,指令杨得志取消了第六次战役的计划,不再准备进行全线的全面反攻。
在无奈的选择面前,美国人只得重返谈判的舞台,与中朝代表在板门店展开对话。1953年7月27日,美国人的傲慢姿态终于有所收敛,他们首次签署了一份“未获胜利的停战协议”。
炒股配资合法吗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